新闻中心
- 传承·守望·致远 人大史学与校友发展主题论坛隆重举行
- “2025年中国世界中世纪史论坛暨常务理事会会议”在我校成功举行
- 历史学院举行世界史学科建设座谈会
- 历史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布干部任免
- 国家文物局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
- 中国人民大学南岛语族与海洋文明研究院成立暨“南岛语族与海洋文明”学术研讨会举行
- 中国人民大学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会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召开
- 人民大学+人民日报社,共同学习!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绎思”学术活动季正式开幕
- 历史学院党委召开巡视整改公开大会暨整改成效综合评估进驻会
- 历史学院2024年“白羽迎新杯”教职工羽毛球交流赛顺利举行
- 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发布会(2024年秋季)举办
- 四方联合共建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签约揭牌暨中国人民大学与江苏省社科联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 戴逸:把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清史事业融为一体
- 讣告 | 沉痛悼念戴逸先生
- 通州·全球发展论坛(2024)分论坛八 “多元文明历程与全球文明发展”在京举办
- 潘基文出席通州·全球发展论坛(2024)并作特别演讲
- 87周年校庆学术活动—— 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学科融合主题报告会
-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首次新时代学科发展工作会议
- 中国人民大学党纪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
- 朱浒:关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
-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员大会胜利召开 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第三巡视组向历史学院党委反馈巡视情况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牢记领袖嘱托·青春奋进今朝”主题联学活动顺利举办
- 历史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讨会
- 历史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总结2023年度工作
- 我校历史学科五项成果入选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拟奖励名单
-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人才制度改革文件宣讲会召开
- 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组织工作会议召开 深化学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系统性改革
- 我院多项重大重点课题成功立项
- 我院两项成果入选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公示名单
- 世界史学位授权点评估会顺利举行
- 《唐宋历史评论》入选为CSSCI(2023—2024)收录集刊
-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 “唐宋史研究的新时代”学术会议成功举办
- 会议报道—中国历史学科自主体系建设规划调研座谈会
- 历史学院参加第六十届田径运动会,取得可喜成绩
-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 我校两项目入选央视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85周年校庆分论坛“学术期刊与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顺利举行
- 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绎思”史学论坛成功举办
- 教育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 “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起师生热烈反响
-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全校干部师生大会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 历史学院赴北京十一学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
- 历史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布学院领导班子任免决定
- 戴逸丨治史入门:我的学术生涯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师生前往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走访座谈
- 一起向未来|历史学院召开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行前座谈会暨出征仪式

从历史的视角理解Covid-19——中英学者对话
2020年11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资助、历史学院承办的国际“云”研讨会举行。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维维安·纳顿(Vivian Nutton,英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成员,以及法兰西学会的外籍通讯成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副教授安德鲁·韦尔(Andrew Wear)、复旦大学高晞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教授以《从历史的视角理解Covid-19》为主题作了精彩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赵秀荣教授担任主持,共800余名师生参与此次会议。

会议伊始,赵秀荣教授解释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第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瘟疫发生时,从来不是医学战胜流行病,政府针对疫病采取的措施和社会的运作方式更为重要。因此,无论科学多么先进、模型多么正确,我们都需要从历史中学习教训。第二,“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在社会运转良好时进行批判性思考,并预测繁荣背后的潜在危机。当社会遇到灾难并且人们感到悲观和失望时,历史学家需要回顾历史,总结其经验,激励人们不要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也不要放弃对生活的热爱。”赵老师说这句话是引用另一位历史学家之言。

维维安·纳顿教授以《与流行病面对面:从雅典瘟疫到文艺复兴时期》为主题发表演讲。这篇演讲旨是将我们目前的状况与历史上三个不同瘟疫流行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时期。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为随后瘟疫的历史叙述建立了范式。他强调瘟疫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医疗问题。第二个时期是腺鼠疫时期(Bubonic Plague)。这种鼠疫共发生三次。一次发生于550年并在东地中海地区持续到10-11世纪。一次被称之为“黑死病”(Black Death),开始于1347年的英国并一直持续到1666年,在西欧持续到1770年,在东欧则持续到19世纪。一次为发生在20世纪的满洲瘟疫(Manchurian Plague)。关于瘟疫爆发最初的解释有神迹的出现、气候的变化等,防疫则着重于强调个人预防。后来的防疫涉及市民行政组织的管理,如禁止外国人入境(最有效),建立隔离区(拉古萨Ragusa,1377年;威尼斯Venice,1448年)和卫生局(拉古萨Ragussa,1398年)。到1550年,还建立了隔离医院(Lazaretto,通常从麻风病医院改进而来)。但也产生了关于什么是瘟疫和严厉的公共卫生措施的价值的医疗争议。第三个时期是16世纪,一个流行病的时代,梅毒、汗热病、鼠疫等传染病接二连三地爆发。它们最开始被解释为一种瘟疫,但随后逐渐被区分。此外,这些传染病也被视为地区性疾病或某种特定疾病——瘟疫是穷人的疾病,梅毒是性传播疾病。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在1546年发表了《传染病》(Contagious Diseases)一书,强调了“种子”(seeds)或“种床”(seed beds)作为传播媒介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有个体携带细菌或杆菌进行传播的方式。弗拉卡斯托罗认为接触传播、空气传播或远距离的污染物传播都是传播疾病的方式,为当时的卫生局实践提供依据。上述三个时期瘟疫的暴发表明,无论好与坏,都必须信任医疗和政治当局,如1576年的威尼斯、1633年的蒙泰卢波内小镇(Montelupone)。最重要的是,在当地对疾病进行调查并迅速做出反应,如托马斯·乔丹努斯(Thomas Jordanus)和1577-1578年的摩拉维亚瘟疫(Moravian Pestilence)。

安德鲁·韦尔教授以《16-17世纪英国的鼠疫和21世纪英国的新冠肺炎:差异与共鸣》为主题发表演讲。韦尔教授认为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死亡率。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持续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流行病使城市地区的死亡率高达20%至25%。而新冠肺炎的总死亡率为个位数,但对于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而言,死亡率要高得多。第二,对疾病的解释。鼠疫在近代早期通常被认为是空气中的一种有毒毒素,来自环境资源,例如污水坑、下水道、腐烂的垃圾、沼泽地上的迷雾等,同时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呼吸接触传播。 第三,措施。针对鼠疫所采取的措施是清洁环境、净化空气并避免与感染者接触。当时的人们认为,将鼠疫患者与家庭中的健康成员“隔离”六周的政策是非基督教徒式的和残忍的,但直到1665年鼠疫结束之前,它一直是政府的政策。20世纪的英国规定,凡患有新冠肺炎的人及其家庭中的任何健康成员都必须隔离14天。与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不同,英国民众对政府这项命令的服从率很低。第四,政府的作用。在近代早期,英国政府并不关注健康和医学。然而,鼠疫到来后,英国政府(如同欧洲大陆的政府)开始参与医疗问题,因为经济和人力成本高到不容忽视。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府早在新冠肺炎出现之前就对本国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尽管与鼠疫相比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要小得多,但仍令许多政府如此关注。第五,政府与医学的关系。在近代早期的瘟疫中,医学的作用是向政府提供咨询,但是医生不制定政策。今天,医学和科学扮演着比近代早期更加重要的角色,科学家可以对政治人物有重要影响。
接下来,韦尔教授指出,两个历史时期的相同之处也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隔离措施,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提供保护以及全国封锁。第二,治疗措施,历史上的疫情与今天的疫情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第三,信息的传递。随着患者人数的增加并越来越接近自己居住地区,人们会感到恐惧。随着数字的下降,人们的信心则会恢复。第四,政府的指导手册。在近代早期的小册子中列出了出门的最佳时间以及如何抵御有害空气等防疫措施。 在新冠疫情中,我们也拥有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的指导。第五,恐惧。在鼠疫爆发时期,人们希望赶走那些可能来自其他传染病地区的人。今天的英国,在许多没有或拥有少量新冠肺炎患者的地区,人们都在抱怨外来人口带来了感染。此外,在新冠疫情中,媒体运用文字和图片制造出令人恐惧的想象力。虽然恐惧存在于所有严重的疾病中,但在流行病期间,它笼罩着整个人口。

高晞教授以《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进化》为题发表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高晞教授梳理了从“瘟疫”到“传染病”的术语转变过程并思考促进现代“流行病”知识转变为全社会公认的基本常识的因素和动机。如同学者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E Rosenberg)所言:“在某种程度上,疾病是不存在的,除非我们通过感知、命名和回应它来同意它已经存在。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直到我们同意将疾病命名为一种疾病,否则疾病就不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在中国,“传染病”一词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传统的“瘟疫”类似于现代的“传染病”。这一词汇转变的过程由传教士、中国学者和中国官员各自采取不同的策略共同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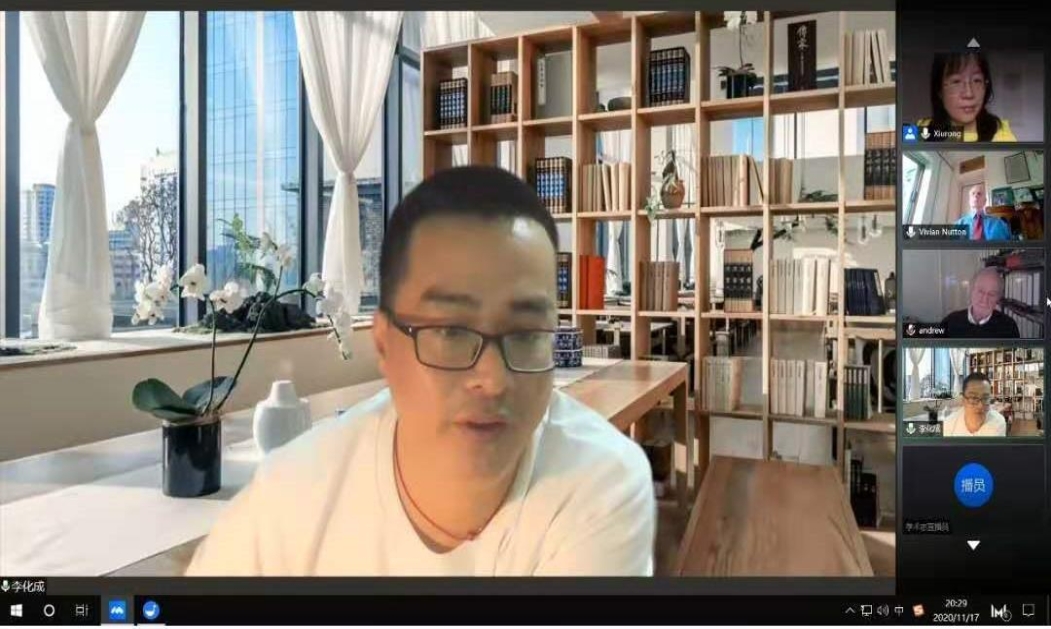
李化成教授以《传染病防治观念的时空差异及影响:从19世纪的霍乱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李化成教授认为,疾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生理异常,而是具有浓厚的社会性。传染病因其流传性广、影响面大,这种社会性也就愈发明显。人类能否控制甚至战胜某种传染病,也绝非仅与医学技术本身有关,而是特定防治观念和行为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中防治观念多为人们所忽视。李化成教授以霍乱(cholera)为例,对传染病防治观念的时空差异及影响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对中国、印度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面对霍乱的不同表现和结果为例,他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疫情防控观念中“社会化”和“个体化”的问题,肯定了社会化防治在疫情应对中的重要作用。李化成教授进而指出,回到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疫情防控的效果与过去相比发生了一个逆转,而这同样是在尚未发现特效药和疫苗的前提下出现的。究其原因,主要不在医学本身,而在于诸多社会因素。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的同时,为什么在历史上率先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的西方国家却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赵秀荣教授对各位的演讲做了简短的评议后,请四位教授就腾讯会议室和直播间(B站和学术志)的老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问题包括如何理解自然的健康;如何理解动物(如蝙蝠和蚊子)与新冠的关系;“大政府”在新冠期间权力扩大,疫情结束后政府的权力是否应该缩减等等。四位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耐心予以解答,他们的回应引发了同学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 友情链接: |
|
| 快速通道: | 中国人民大学 | 人大新闻 | 国际交流处 | 研究生院 | 科研处 | 招生就业处 | 教务处 | 图书馆 | |
